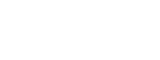雷国定:养羊
养羊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畜牧局杜股长向我介绍了养殖“小尾寒羊”的养殖事宜。
他说:小尾寒羊属于蒙古羊亚型,成年公羊体高近一米、体重可达80至150公斤,母羊体高约80厘米、体重50至75公斤,而且繁殖能力很强。我有些疑虑:“寒羊”在咱们这儿能适应吗?他解释道:寒羊的祖先本是古代蒙古羊,宋朝时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南迁,逐渐引入了黄河流域,肯定能适应这里的气候。他还说,养一只母羊年收入能达到3000元。那时人们月工资才几百元,这个数字让我十分心动。
之后,我又到山西农业大学请教了高教授,他不仅给了我一些资料,还提到他有几个学生在山东的农业部门工作。
没过几天,我便跟着杜股长到了山东梁山县——那里是小尾寒羊养殖基地。我们扎下收购点,在当地畜牧检疫中,收购农家的小羊。听说离“水泊梁山”不远,我给收购的同事买了条烟,便独自去看了当年的“梁山寨”。

这一趟,我们一共买回两大车小尾寒羊。我分了十只,还给梁坡底、彭披头的朋友各带了几只。
买羊容易,只要舍得花钱,再花上几天时间就能办成。
养羊却难了。羊买回来了,往哪儿圈?吃什么?谁来管?这些问题之前都没细想,当时只想着挣钱。
那些年,我确实太需要钱了。自从1985年起,我所在的供销社效益就一直不好。私营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他们不受政策限制,也没有历史包袱,是轻装上阵。而我们呢?哪怕一件商品调价,也得主任批准,甚至要跑到县社或物价局去审批,等手续走完,商机早错过了。再说,供销社还背着二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历史包袱,要供养退休职工和其遗属。比作竞争,我们就是扶老携幼和正常人赛跑,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。
我家院子里有三个腾空的猪圈,暂时把羊圈在里面。父亲每天帮我把羊赶出去放牧,眼下的问题算是解决了。
我信心满满,每隔几天就抱着小羊一只只过秤,越秤越高兴:公羊每天能长八两,母羊每天可长六两。就这样一直称到它们长成一百几十斤,我抱不动为止。
要想长期养下去,必须保证充足的饲草。多方打听后,我种了四亩苜蓿,第二年就长得郁郁葱葱。我隔三差五去割上一车,回来用铡刀切碎备用。
还得准备过冬的草料。下班后天已黑透,我和妻子拿上几条大编织袋,拉上平车,借着月光在树下扫落叶。把一堆堆树叶装进袋子,填得结结实实,再用绳子把这几袋捆牢在车上拉回家。虽然干得是力气活,却一点儿也不累,反而觉得那一大碗米汤和几个饼子格外香甜。

夜间下了小雨,第二天早上照常扫树叶,一种激情下,根本没察觉到与往常的不一样,当我把树叶装满大袋子再往车上装时,乍也挪不动袋子,原来是淋湿的叶子上沾满了泥沙。正好来了两个后生,帮我抬到车上。他们说:一袋子足有三百斤。
大小二三十只羊过冬需要大量草料。我抽空联系了种玉米的村邻,刨人家的玉米秆喂羊。因为白天还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单位上班,我只能天不亮就骑摩托车赶到远离村子的玉米地。月光下,四周都是阴森森的玉米秆,满世界静悄悄的,只有我刨玉米秆的“沙沙”声。镰刀挥过,一片片玉米秆应声倒下,藏在其中的几座坟茔露了出来。我不知疲倦地继续干着。两小时后,月光渐淡,天边隐隐发白,我很高兴:还能再干两小时。
这些玉米秆虽是喂羊用的,但按老习惯,我还是叫它“柴”。瞅零碎时间,我把柴用湿谷草扎成捆,再花整天时间拉回来。我开的是18马力的柴油三轮车,车身高,车厢宽敞。把一捆捆柴有序码好,再一层层摞起来,保持平衡,然后在车尾的柴中间,深插一根木锥,在木锥下的车身上挂一个人字木架,套在木锥上,再从车厢前套上两根钢丝绳,也套在木锥上,这样就把一车柴固定成一块,再用一米左右的木杆以杠杆原理绞木锥上的钢丝绳,一圈一圈,绞得紧紧的、稳稳的——因为稍有不慎,就可能掉下柴捆甚至翻车。从地里拉回的柴太多,自家房前屋后堆满后,还得往邻居家地盘堆。柴柴草草的,既占地方也不好看,现在想起来,真多亏了好邻居们的包容。

喂一两只羊用铡刀切草就够了,如今养了一群,我买了切草机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花上一整个上午或下午,用切草机切柴。看着一把把柴被机器吞进去,又从扬升口密密麻麻地吐出来,真觉得过瘾。但另一方面,整个场地尘土飞扬,尽管戴着防尘面罩、穿着严实的工作服,待久了还是一身尘土。连续几个小时像机器一样不停地搬柴、输草,出力多的那条胳膊都肿了。当把一大堆柴都切成碎末,清理好场地,洗净身子后,总会产生一种登上山顶的清爽之感,让我久久地舒畅。
小尾寒羊不仅长得快,产羔也多。一般一胎能生两到三只,最多的一胎生过六只——相当于养一只小尾寒羊顶得上三只普通母羊。一个大年三十的半夜,听到南面羊圈里的“哼哼”之声,我赶紧起床出去看,原来是一只母羊产下了三只小羊。因天气寒冷,怕浑身湿漉漉的小羊冻伤,就把它们都引回了屋里。这时,“三羊开泰”这个词突然浮现在脑海——虽然“羊”不是“阳”,但此情此景,我觉得“羊”和“阳”就是一个意思。
我家的种公羊有二百几十斤重,长着又粗又长的角,愣头愣脑,能把埋在地里的铁棍用头顶进土里,劲头大得像个铁锤,生人都不敢靠近。有一段日子,它总试着用角顶人,也许它只是想和人玩玩。时间一长,我有点后怕:万一我父亲放羊时被它顶一下,那可不得了。怎么办?确实没好办法。总想教育它一下,但我不会用鞭子,用棍棒又怕打坏它,我就把绳子拧成麻花状,蘸了水,再把公羊摔倒在地,单腿跪住,一只手按住,用这“油麻花”绳子狠狠地抽它,直累得我喘不过气来才停了手。那天里,它再次见我时,满眼流泪,向着我双腿跪地不起。我一下子心软了,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,还是后悔不已。
那几年,小尾寒羊养殖正热,经常有外县甚至外省的人慕名来买羊。我养的小尾寒羊虽然没有预期的效益,但比养本地羊强多了。一只三十斤重的小羊能卖600元,现在想起来仍然高兴。
因为还要上班,实在没有精力继续养下去,最终恋恋不舍地收拾了这一摊子。
事后,我常常想起这段经历,也分析过小尾寒羊出肉率低的问题:它长得快,就需要相应的营养跟得上,而我们这里草资源不足,假如给配足饲料,就会提高出肉率。另外,养纯种小尾寒羊,其实还不如养它与本地羊杂交的后代效益好。
虽然是“事后诸葛亮”,但对其它事情也应该是个启示吧。
2026年1月29日
(图片来自于网络)